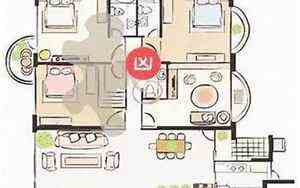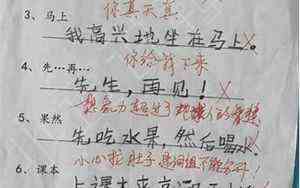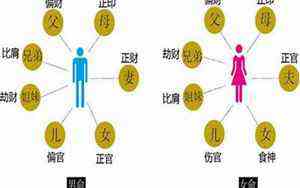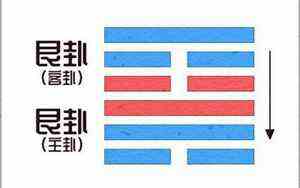你敢裸奔吗?梦见自己浑身赤裸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你敢裸奔吗?不管你在现实中敢不敢,或许你在梦里这样做过。
梦见自己和他人赤裸相见,心里可能是很尴尬的,想极力掩饰,但旁人却不以为然。这样的梦也有多种解释,男性梦见自己裸体见人,可能是想掩饰什么弱点。裸体一方面意味着性欲的刺激,一方面也象征着对自然真我的渴望,不受约束,回归一种真诚的状态。
梦见自己浑身赤裸可能只是一个警告 :“你旅行所需的衣服准备好了吗?你该洗的衣服洗了吗?小心,你会没有衣服可穿的。当然,就算你忘了带换洗衣服,你也不至于像梦里那样,赤身裸体上街,可梦中的自己就喜欢用这种形象的方式来和你说话,用这种夸张的方式和你说话。
裸体还表示真诚、坦率和不欺骗。《围城》中一个风骚女子鲍小姐被称为 “局部真理”,因为“真理是裸体的”,所以半裸的鲍小姐就是局部真理了。有个笑话说一次罗斯福闯进了丘吉尔的浴室,赤身裸体的丘吉尔为掩饰窘況,灵机一动摊开双手:“大英帝国的首相对你是毫无掩饰的啊。”
如果你自己就常梦见自己裸体,请并不为之羞愧。因为裸体表示的,是你对别人的坦率真诚。
裸体还表示自己被人看穿。据说有位大学讲师常梦见自己在校园散步或在阅览室里看书时突然觉得人人都在看他,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只穿着袜子和鞋。通过解梦了解到,梦者对自己评价解梦,认为自己的论文都是有欺世盗名之嫌的。因此,他常常处于怕“被人看穿”的恐惧中。
弗洛伊德在分析裸体的梦时,指出裸体的梦是对童年时的快乐之一,即对不穿衣服的快乐的怀恋。而且这种梦也是梦者在与其关系密切者面前想裸露的表现。弗洛伊德的这种想法也与他对梦的基本看法有关。“裸露”是性愿望的—种含蓄的满足。
此外,脱衣服或裸体的梦往往是与性有关的。梦中脱衣服时自己的感受或发现自己裸体时自己的感受,正表明你自己对性的态度。是坦然接受,还是为之窘迫。梦见自己裸体时的情绪感受是愉快的,表明梦者对性的态度较坦然,没有什么性压抑;反之,则表明梦者多少对自己的性愿望是不愿或不敢面对的。
一个国外的例子:某人梦见老师赤裸,而且阴茎很细小。心理学家分析,这个梦表明他虽然很敬佩这个老师,但心里暗暗觉得他不够有男子气。
梦中别人对待你裸体的感受,反映着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你的真诚或对你的性欲的看法。梦中有时会有裸体的异性出现,并且晚起梦者强烈的性冲动,这种梦不领再解释,只是一种满足欲望的梦而己。在青少年中,这种梦是很多的。
如果做梦人梦见自己尽管浑身赤裸但却心无所动,坦荡荡的,说明做梦人心无杂念,不惧怕任何事情。
梦到一个女人光着身体什么意思/有什么寓意/意味什么/好不好?
梦到一个女人光着身体什么意思/有什么寓意/意味什么/好不好?
编者按:世上万事万物皆有迹可循,只要深入其中,一切都会变得清晰明朗,譬如地震来临前鸡鸣狗叫,一个家庭分崩离析前内部不和,一家公司倒闭前资金链断裂、人员大量离职等等。一个人做梦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实际上梦境包含着未来的密钥。作为普通人,当珍惜上天给的提醒,顺势而为,趋利避害,欲成大树莫与草争,遇烂人及时抽身,遇烂事及时止损,遇破财及时化解!
一位男士问:昨天晚上梦到一个女人光着身体,整个梦境就跟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样,是不是有不好的寓意,又或者有什么启示?
何天叔答曰:根据《周公解梦》一书,“妇人赤身主大吉”,意思是梦见女人光着身体,表示遇事顺风顺水、大吉大利。
此外,根据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的理论,梦是欲望的表达,“现实中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会以更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经了解,在现实生活中,这位男士有一位女性朋友,双方都互有好感。在做梦前一天,他跟这位女性朋友去游泳,中间有很多身体接触。第二天做梦,正好梦到一个女人光着身体,其本人一些不良的想法在梦境中得以实现。
中国大卫-裸像
也许,作这样的称谓是多余的。大卫是大卫,你们是你们。
将你们比作大卫,或许大卫比你们,实在是出于无奈,中国暂时还没有与你们业绩相近又装束相同的英雄豪杰,更不要说这类英雄豪杰的高大雕像了。神州的偶像们穿戴太多,多到成了文化遗产。牧羊少年大卫,原本是穿着衣服抛出克敌的石头,但米开朗基罗给剥去了,于是,这尊大卫供后人瞻仰并留给世界艺术史的,便是他裸露出来的深邃内涵。在这里,请允许我们为你们塑一座赤裸的群雕
应该塑上他。
他靠着洞壁半躺半坐,似睡非睡。他是你们中的一员,他和你们都一丝不挂。不光是热。潮啊,潮得厉害,防潮被能拧出两斤水,何况衣服。洞底的积水刚刚退去,南国的雷声又通知迎接一场更大的暴雨。地面精滑,上行的老鼠进两步退一步。人也能发霉,譬如你们中的他。他耳轮包了层绿苔,面带菜色的头颅像一件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裆烂了,脚丫也烂了。脚趾泡得糟白,一揭一块皮肉,如同浸了水的胀馒头。脚趾间白皮的裂隙深处,能窥到粉红的底蕴。老鼠用发霉的鼻头碰碰他的脚,找不到一片坚韧的茧皮可供磨牙。他用手抠抠裆,指甲也是软的。烂裆这词不如烂脚丫来得具体,裆太笼统,就像把烂脚丫说成烂下肢,烂运动系统。烂裆,是弥漫在阴囊根部的溃烂,痛痒交集,要多受罪有多受罪。坐,卧,和走,都要支叉开双腿,仿着一架合不拢的圆规。脚怎么办?遍地的水渍,脚一沾地就犯疼,穿鞋跟受不了,再说也没鞋,解放鞋的橡胶部分全让老鼠当茧子磕了。他有办法,没办法就不是他了。人到没办法时就有办法了,所谓没办法是逼得还不够。你们不有的是编织袋吗?同尿素化肥袋的区别仅是颜色,军绿色,装上土封堵洞口用的。这就行。
他动了。搬起左腿,套上一只编织袋。搬起右脚,套上一只编织袋。拔起身体,立稳,两脚分成八字,两手提编织袋口。你们漠然注视着,谁也不上去帮他一把,目送他摇动鸭步向洞口挪。他的瘦屁股泡得挺白,你们想,也就看到了自己。他哗哗哗哗办完事,转身向回摇,提着那无裆的裤腿,不,过膝的筒靴,不,活动的地毯,会享福呢。
又突地,洞外枪响。轰!手榴弹。你们,他,一群裸人,全没了痛苦,抓武器,扑到洞口,表情严峻得让人掉泪。
至于他,塑不塑上无所谓。
有战斗英雄的称号,不等于是老前线。他看你们奇怪,你们看他也稀奇。待到他不奇怪了,你就进入了英雄行列。
向小平衣冠齐整向一线走,路过一个炮阵地,炮手们全部赤身操作。他惊讶地问:“你们怎么两个裤头也不穿?”炮手们瞅瞅汗水浸透军衣的向小平,像看穿棉衣棉裤进澡池子的傻二哥。
他又来到你们的一部分人当中。在小水坑边,他遇到本连的第一位裸人是军医。
军医大的雄性美相当充分,瀑布般的络腮胡挂下半尺多长,宽阔的胸膛生满奶油小生们嫉妒的胸毛,又有猫耳洞给怂恿出来的长汗毛,乍一看,向小平差点叫你们“野人”。
向小平问:“怎么裤头也不穿,都光着屁股?”
军医以你们裸体人的自豪说了你们的一句名言:“这就是光屁股蛋儿的地方。”
听听,屁股蛋儿,只有你们老山前线对臀部才叫得出这亲切的昵称。军医刚从军医学校毕业不久,临参战才抽调过来的,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几个月就俨然是高阳酒徒,连口语乃至口气都不仅基层化而且前线化了。
向小平逗他:“越军女的发现,可给你们抓过去哟,老越可有寡妇连。”
大胡子军医说:“正因为有寡妇连,咱不穿裤头,才不打我们。”
妈的,在一线,事儿都颠倒过来了,接受这种颠倒很不容易。向小平坚持穿裤头。穿裤头是要付出代价的。热。热也穿,毕竟是人,祖宗还晓得挂树叶围兽皮呢。
他四下游击,冷枪手本无固定位置。穿裤头显然有些特殊化 配合他打冷枪的弟兄们全都一丝不挂。他看出来,排长们最联系群众,去连部开会,钢盔往头顶一扣,叨上颗烟就齐了,光腚去,光腚回,好像上了趟茅房。连队干部有的光腚,有的不光。穿裤头是一种身份,营团干部穿裤头率占百分之百,大檐帽、肩章和黑皮鞋不穿可以,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崩溃。向小平怕兵们说他冒充干部,但还有别的可怕的,两种怕产生内耗,裤头留在向小平身上。
他照例对受教育最多又退化最快的大胡子军医表示不敬。他们住邻洞,来往密切。洞口极小,向小平瘦小,进出自如,大胡子军医稍壮些,进洞必须先卧倒,脚腿先进,再挪进臀部,再上身,再头。向小平常常在这里恭候,军医的臀部进来时,就用树枝突然一戳。洞内多蛇,时不时还能见到白尾梢的大蝎子,屁股上冷不丁来个动静,军医打个激灵,蹿出洞,摸摸屁股上没什么损失,朝洞里吼:“哪个?”哪个他也奈何不得,要想发作,向小平一把抓住他的胡子说:“敢动?”军医马上就求饶,每逢这时,向小平训他:“叫你光屁股蛋儿。”军医以大胡子为荣耀,你们裸人世界产生了三个大胡子冠军。军医是络腮胡的代表。通信连有个电台兵是卷胡子代表,胡子像在理发馆烫过,常被你们用来作一些不雅的比喻。山羊胡代表是五连长。一次,三个大胡子凑巧都到集团军开会,集团军政委闻之,专门去看望他们,并合影留念,也是大胡子军医不怕向小平讽刺挖苦的动力之一。
大胡子军医没能感动向小平,向小平是被他自己打败的。
洞内缺水,常常发生洗裤头还是喝到肚子里去的痛苦抉择。裆里捂出了痱子,奇痒难挠。要屁股还是要面子的权衡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你们好办,先上到阵地,大家一起脱,彼此彼此,在同一起跑线上。向小平不行,这个阵地他来的晚,来晚了还穿着裤头到处取笑裸人,在他的冷枪战果中,还有一定比例的对方裸人(一律男性)。你们这群裸兵同仇敌忾,倒要看看他向小平能坚持多久,更要看看他去掉裤头后,要害部门与你们有何区别。向小平知道你们的险恶用心,可说到底还是要屁股要面子的问题。他看到一个信仰相同的穿裤头者,患了烂裆,裤头粘连在皮肉上,当裤头终于脱下来时,一层烂皮也带下来。既没保住面子,也没保住那地方。只一下子,向小平的裤头就褪下,大摇大摆走出去,尽管心理发虚,奇怪的是,你们没人拿他打趣,甚至还有遗憾:看不到穿裤衩的人,就像看不到珍稀动物。
向小平加入了你们的行列,也加入了你们的思想体系。掀开外在的东西,人都差不多。他可以用老前线的资格嘲弄新来的穿裤头者。表面上,是穿裤头者奚落无裤头者,但无裤头阶层的沉默是对有裤头阶层的更大揶揄。这一切,穿着裤头是体味不到的。自从和你们保持了一致,向小平的安全系数也增高几倍。越军的观察所到处捕捉冷枪手,冷枪手就在他们眼皮下光着屁股蛋儿东奔西忙(不扛狙击枪,枪不敢露出来)。对光屁股的人,他们也开枪,但不会轻易赏给几群迫击炮弹。向小平也是如此,见到用服装炫耀身份的敌军,一定要优先赏粒子弹头。越军女兵例外,女兵们平素不裸,可洗澡,上厕所,全不遮挡,洗完澡还朝这边摇摇毛巾。
他——潘玉琪,看看他的关系网,便知该不该进猫耳洞人群象中。
集团军政治部朱增泉主任,马师长,陈政委,王团长,李政委,军师团三级首长是他的朋友,一个战士得到的殊荣,令全集团军的营连干部们望尘莫及。而且,都是各级领导主动找他,可见神通之大。
全裸状态的他,是很男子汉“派儿”的。一米八0的个头,鼓挺的肌肉群,匀称的骨架,方头大眼,穿上军装的他便没这等魅力,你们肯定赞同这个评价。
他喜欢歪戴帽,敞风纪扣,眼里一股邪劲,谁见了谁头疼。不然,他这个领头的后进战士,怎么能结交那么多领导呢。
潘玉琪裸着躯体举起入党宣誓的拳头,他又裸着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群行列。从决定不给予劳动教养处理到这新的一步,间隔仅几个月。与其完全归功于战场对心灵的净化,倒不如同时也承认他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孤胆,组织指挥能力强,机动灵活,能吃苦,好动拳头,对敌人动就是英雄,对自己人动就是混蛋。后方没敌人,打的全是自己人,他不当后进战士又能让谁当?衣冠不整,在后方军营算是恶习,在前线一裸,没那么多啰嗦事。他天生是打仗的料,他天生是在战火中改变命运的料,看看他裸着有多么可爱,过去,他穿着衣服时,就有多可气。想必也有领导同志看人眼光的净化,不然,在后方已经修炼和净化得很到家的一些人,岂不应比潘玉琪还要好上一大截。
是宣传科科长刘学公上阵地了解情况,见到了裸体奔过来的潘玉琪。你们多数人未必能有机会与科级干部结下私交,虽然你们也裸着,潘玉琪就行。他握住刘科长的双手,使劲摇了十几下。科长问他,老毛病又犯了吗?他说没有,快一年了,没向自己弟兄们动过手,小小不然骂几句是有的。阵地上见熟人比什么都高兴,潘玉琪比比划划讲,吹。刘科长眼睛不敢向下移,眼对眼看着听人家说话又是件累事,刘科长不断点头,放到哪都不自然的两只手揪衣服上的线头。
约摸谈了十几分钟,潘玉琪不知从哪个茬儿引起顿悟,大叫:“哎哟科长,你看我,真不像话。”双手捂住了“司令部”。科长连说,没事,没事,却忍不住笑。潘玉琪像一个讲实惠的外国球星,不管全场男女球迷的观瞻如何,两张大手往裆部一盖,勇敢地挡住门前任意球的9.15米处。潘玉琪说:“科长等等。”捂着转身跑开,不一会儿回来,堂而皇之地装备了一条裤衩。
让潘玉琪这么捂着塑在你们中间,好么?
真实,独特,又有良知。
潘玉琪很快变换了姿态。
那是我们老山之行的头一个星期的一个傍晚,在师作战室,旁听作战交班会。值班参谋汇报:A二团排长潘玉琪修工事触雷,左脚负伤,送到师医院抢救。潘玉琪是我们的采访对象之一,我们想见见他,不巧,他已转送野战二所,听说情况尚好。
潘玉琪躺在手术床上,眼睛里迸出无影灯的斑斓光点。他想不通,那地方平平常常,一脚踏上去,就把脚炸得骨碎肉烂。确认不是做梦后,他心理泛起一层淡淡的迷惘,还有遗憾。弟兄们围着哭,他笑着被抬上担架,说,没事,很快就能回来,我都没事,你们哭个哪门子。没到雨季,这季节衬衣还穿得住,他是穿了衣服的,到医院,就给剥去了,用剪子一片一片剥的。他又裸了。女护理员剪他的裤衩时,他很不情愿,几个月没洗澡,埋埋汰汰的,让人家姑娘给拾掇,他害起臊来,闭上眼睛,两只手很想移下去捂住那儿。等以后出了院,再见到这些姑娘,一米八老爷们儿的脸往哪揣呀。
军医用清水冲刷他的伤腿,泥是红的,血是红的,红水淅淅流下,夹杂了碎肉和骨渣。伤口毕现。脚完了。用何等的想象力,也不能把眼前的筋筋络络还原成脚的意象。爆炸力向上传导,小腿骨劈裂,糊状的骨髓把红肉丝紫筋条染得晶莹。没血色的皮肤还看得过去,里面的肌肉组织却松散得象坏了瓤的西瓜。小腿无法保留。局麻。刀刃贴着骨头,又一推一拉变角度,软组织上下脱节。锯骨的钢锯是管工通常用的那种,锯身和锯条经过高温消毒,用起来得心应手。锯齿与腿骨的摩擦声在潘玉琪听来,象很远的地方有一台水泵在工作。
让潘玉琪支着一根拐杖立在前排最中间,你们一定认为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那条腿按炸伤还是按手术后处理,这要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野战二所收过潘玉琪,又送走了,送行的有政治处副主任,营教导员,组织干事,军医。
清明节,我们在殡仪馆的一间供满鲜花烟酒的小屋里见到他。他身穿军装,隔着玻璃看我们。他一米八的伟男子,睡在一尺见方的大理石骨灰盒里。他依然裸着,服饰的灰烬早随蒸腾的烟气从高大烟囱夺路而去,他留给后人的是烧炼后高度纯化的裸骨。
塑上他,为他塑一座山峰。
塑上你们,活着的和死去的南疆裸体人,为你们塑一条山脉。